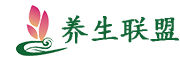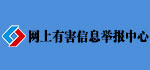学术风气的转换,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曾经辉煌一时,涌现了不少经典力作,不过五十年铅华落尽,日趋无声无光。好在不断交叉与演进的学科点又千帆万树,从环境史切入城市史,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生领域。侯深的《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以其多年环境史的砥砺,放宽视野看城市,就是这么一部应运而生的作品。
一
“无墙之城”之所以被作者当作美国城市的核心意象,是因为在该书看来,新大陆广袤无垠,由于建国较晚,从来没有所谓的城墙,更可以无拘无束地向外扩张,这也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古老城市的开放、包容气质。
《无墙之城》从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现状说起,走出所谓“地方感”的城市史研究,视野宏大,个案细密,呈现了整个美国城市环境史的风貌。全书分为城市书写、增长的城市、扩张的城市和城市的思想景观,“城市书写”梳理了城市环境史的发展过程,提倡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应当打破城市的边界,将城市的历史与广阔的生态演化的历史勾连起来,寻求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互动。“增长的城市”聚焦城市内部,探讨美国城市内部的环境史,同时以波士顿为例,探讨波士顿为不同形式的自然寻找其存在的位置,以便重新定义文明在城市时代的内涵。“扩张的城市”则关注城市与其之外世界的关系,探讨城市如何改变了城市之外的自然世界,如何双向地影响。最后一部分,从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入手,对于城市主义与反城市主义都做了反思。
无墙之城,注定了扩张有时是没有边界的,资本的力量迅速扩张,工业化带来重度污染,资本家获利颇丰,产业工人、城市贫民却惨遭不幸,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后遗症。美国也不例外。尽管美国国父之一的杰弗逊在立国之初,曾主张将肮脏的城市留在欧洲,让大洋彼岸煤烟笼罩的世界成为美国这片洁净、清新的农业之土的工厂,但事与愿违。
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注意到:“整个19世纪,美国人都把烟与煤带来的所有积极变化联系在一起:生产、繁荣和进步。对于许多依赖肮脏的软煤的城市居民来说,烟流就像文明的旗帜一样,从工厂烟囱、机车和蒸汽船上升起。”这种乐观主义背后,其实是很多城市的重度污染。在作者看来,“造毒与罹毒是现代城市的共性”,以工业城市匹兹堡为例,“那些在夜晚来到匹兹堡的人首先看到的是矗立在他们面前的黑色山峦,在其侧,有六团燃烧的火焰,排列成行,如同六只热烈的眼睛”,整座城市甚至被称作“掀开盖子的地狱”。芝加哥则是扑面而来的城市烟尘与屠场恶劣的气味、污水、嘈杂,这些阴影与都市繁华如影随形。
好在,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仅仅聚焦工业化,也对环境保护开始留意,大批专门人才纷纷加入,兴建道路、铺设铁轨,开凿运河,修葺堤坝,同时也护林植树,整饬河道,分配水源,保持土壤,追求双重理性化,“不仅要剔除自然本身的各种无序与可怖的因素,也要修正美国传统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浪费”,尝试用科学的曙光拯救沉沦的自然。二战后,美国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入消费社会,环保运动也由早期以效率为福音的资源保护转为以生活质量为旨归的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总是很难两全其美,环保政策触及消费者与经济集团的根本利益,后者往往会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对待自然态度的制度与法令,要环保还是要美元,最后,善良的愿望往往被迫一退再退,因为“主流消费者的梦想正是美国梦想之所系。独栋住房背后的信息是对私有财产神圣地位的捍卫和对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渴求与实现”。“当政府力图对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时,很多的法令将对业主在其私人领地上的行为进行管制,而这一点遭到了业主与舆论最为激烈的抗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美国立国根本的背叛与侵犯。”
可是,进步主义改革者却不这么看,面对田园主义谢幕、城市时代来临,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恐慌,甚至对现代文明的走向及其基石——科学的质疑声音此起彼伏,这当然无法抗拒强大的科学时代的铁幕,不过他们的警醒,却无形中推动了环境保护的深化。
二
19世纪后期,在大西洋两岸都兴起了一股反思文明进步是否有些过头的浪潮。新大陆的好处在于,由于地广人稀,同时也允许某种“异端”存在,比如《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大卫·梭罗愤于工业化的触角无所不在,使得其居所同其他新英格兰城镇一样变得刻板而僵化,于是他选择离群索居,试图寻找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渴望了解一个完整的上苍和一个完整的地球”。梭罗背后有着一群人,以异端的身份,批判工业化的无所不在,期望能保存更多自然的野性。
《无墙之城》注意到19、20世纪之交大西洋两岸对于环境改变的互动,美国旅行者从欧洲归来,或心仪巴黎的恢弘、典雅,或慨叹德国城市的整饬,或在英国花园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见贤思齐,回到家乡,不少人为自己城市的粗糙、肮脏、缺乏统一感到羞愧,期待从欧洲城市风格中找到改造城市公共空间的蓝图,进而开始创造表达自身特质的城市——现代性的都市,保护或改造荒野、城市飞地,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第一个城市公园——纽约中央公园的设立就是其中典范。最为难得的是,美国由此建立起了一整套保护荒野的法律、机构与制度,甚至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一过程充满了各种博弈与杂音,自中央公园的修建被列入纽约市政议程之日起,其合理性就受到各方挑战,涉及经济利益,也涉及草根阶层的社会公正,因为公园的修建导致后者流离失所,沦为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牺牲品。可是推动建造者不这么认为,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的设计者查尔斯·艾略特就觉得,富人有时间逃离城市享受自然美景,但是深夜奔波的城市贫民,一样期待有机会欣赏自然风光,却没有这样的财力与时间,城市公园恰恰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精英阶层尽管面临不少指责,依然推动了这些计划的落实,以后见之明来看,无疑是整个城市的多赢局面。
当时的城市管理者为了公共利益,放弃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让这块宝贵的地皮成为公共空间。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央公园反而注意留白,让人与动植物得以在其中诗意地栖居。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杰瑞·科瓦尔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公园对于生活在纽约的居民非常重要,它就像这座城市里的绿洲。它是都市人暂时逃离城市喧嚣的庇护所。如果没有中央公园,曼哈顿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公园的设计影响了很多城市公园的建造,让城市更有包容性与亲切感。
公共空间诞生之后,想象力随之而来,中央公园开始成为《蒂凡尼的早餐》《博物馆奇妙夜》《马达加斯加的企鹅》《复仇者联盟》的取景地,留下菲茨杰拉德、伍迪·艾伦、鲍勃·迪伦的足迹,甚至《纽约客》杂志有不少以中央公园为背景的封面。从自然景观的改造到文化景观的塑造,纽约中央公园成为一个立体的纪念碑。
类似的环境改造比如公园运动、城市自然化运动,在美国城市史上多次出现。此前的工业城市环境逐渐复苏,波士顿风光依旧,匹兹堡重现蓝天,堪萨斯城重新崛起,旧金山也变得适合各种生命栖息,之前的无序扩张有所收敛。当然,除了自身环境改善,这其实也建立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那些消失的污染只是转嫁到了其他国度而已。
这是一个更宏大而更复杂的问题,关涉“新的城市,新的人民”,虽然远超新大陆的范畴,但寰球同此凉热。
三
环境无处不在,环境史立足于研究不同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理解人类所处、所做与所思的历史,无论是城市史还是环境史,建设者、破坏者、承受者、参与者、旁观者,都是人,如果没有人,就没有这一切。王汎森先生曾说:“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好像结构性的力量强大到你无法打破,可是终究还是有人可以把它扭转过来,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勇气,得到一种智慧。”
新大陆的创立者——“五月花”号的乘客本身就特立独行,在侯深的叙述中,我们也看到诸色人等的反思与努力,他们面对工业化嘉年华的狂欢,有的选择离城索居,有的选择环境修复,有的选择大声疾呼,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发展,没有变成一个固执己见的单向列车,而是多向的交织与喧哗,所以才有工业城市的重返青春。
19世纪80年代,伴随“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的兴起,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大城市中的部分中产阶级开始反思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革新寻求新的秩序,比如改良城市环境,保护自然及其资源,改善贫民窟的环境,关注水和空气的化学污染为人体带来的危害。一波一波的改变,既揭示出城市的病痛,又试图提供解毒剂,城市与人类如此密切地融合在一起。
这里面的自我纠错与修复,涉及根本制度安排,但如非有有识之士的努力,其实也相当可虑。这一过程往复曲折、矛盾丛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但是有识之士的振臂疾呼却时时出现在叙述中,例如《沙乡年鉴》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常年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创立了著名的荒野协会,该书就是他对在沙郡进行的生态恢复实践和各地荒野地带游历的总结。这一名单可以很长,无数人的使命感,促进了美国城市环境的更新与活力,这里面不乏清教的因素。
“新鲜的事物不断地涌入这个世界,而我们却容忍难以置信的麻木迟钝。”(梭罗语)从纽约开启的城市森林,日渐辐射于世界每一个角落,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世界,俨然成为每一座城市的标配,身处其中的人,似乎变得微不足道,然而,这毕竟是人类的城市,我们不能麻木迟钝,面对无序而粗暴的扩张,我们值得为这方生命栖息地做点什么。
正如沃斯特所言:“美国人对大平原仅仅一个或两个世纪的统治,并不能成为预言任何社会或机制可以长期生存概率的根据。在如此短暂阶段的基础上,没有历史学家、环境史家或其他人,能够挑选出一个未来的赢家。”我们还需要不断倾听自然的声音,要知道人类文明史,不要说因为环境的恶化导致城市的衰败,甚至使得某些文明消亡。
侯深的母亲是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翻译了不少环境史经典,侯深很早就对环境史有所了解,又赴美师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先生,可谓深谙环境史个中三昧。《无墙之城》关注最新研究动态,包括2020年的国内外博士学位论文。在史料运用方面,虽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无法返美查阅档案,但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档案却得以充分利用。在文献收集方面,作者下了大功夫,加之文采斐然,让阅读体验甚为美好。
对于城市环境的未来,侯深相当乐观,她期待“唤醒城市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分享的坚韧生命力,从而帮助现代世界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即使比之从前任何一刻,它都是一种更加脆弱的平衡”,这其实需要人类的自我克制,充满善意的心灵,才会赢得更加美好的环境。